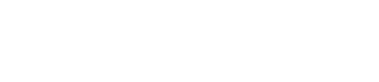日前,第二届“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”评选结果揭晓,我校徐真华校长成功当选。为此,《羊城晚报》记者何晶专题采访了徐真华校长。
以下专访内容转载自《羊城晚报》。
何晶:在您的学术生涯中,您个人最重视的学术成果有哪些?
徐真华:我的学术成果有两部分,一是法国语言文学方面,我个人更看重两本书,2001年出版的《理性与非理性:20世纪法国文学主流》,2002年这本书被国务院学位办评定为研究生教育推荐用书,很多学校的研究生在用这本书当教材。另一本是《法国文学导读——从中世纪到20世纪》,这本书被列为“十一五”、“十二五”国家规划教材,有30所院校的法语系在使用这本文学教材。对我来说,老师愿意拿来当教材,学生喜欢用,这就像是获奖一样让人高兴,说明了它的价值。
另一方面是最近十几年在研究高等教育管理,以改革谋发展,规范办学、人才强校、特色兴校是我的治校理念,实践也证明了这对广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我也发表了一些高教管理论文,这些论文更多的是根据我的行政实践来写的。我认为今天的高等教育应有远投的目光,培养高素质的全球化公民。
何晶:您的治学之路是怎样的?师承何处?到目前形成了怎样的学术脉络?
徐真华:我是老三届中学生,1972年被推荐到原广州外国语学院念书。可以说我是广外土生土长的学生、老师、校长、党委书记。70年代广外法语系有50多个法语老师,这些老师对我们像家人一样,严谨治学、认真负责的态度,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我的博士生导师黄建华就是其中的代表,他对我做学问与做人的影响非常大。
大学毕业后的四十年,平均我每工作七、八年就会出国进修两年。从70年代到90年代,我分别去了摩洛哥王国穆罕默德五世大学、巴黎新索邦大学、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进修,回国后跟随黄建华老师攻读博士学位,博士论文《新词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》已于2001年在法国出版。
从2000年开始,我开始担任广外校长。当时我表态,我的第一专业是治理好广外,第二专业才是法国语言文学。平时上班时间我以第一专业为主,寒暑假做第二专业,肩上挑了两幅担子,一直到我退休,现任广外资深教授。
何晶:在您及同行的努力下,您所在学科的研究基于全国学界何种地位?
徐真华: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,在全国可以排到第一梯队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这其中的法国语言文学,也在第一梯队,在华南片区可以说是力量最强的。
何晶:在讲究实用主义的时代,您认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发展前景如何?
徐真华:我有一些担忧,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,政策支持技能型大学的发展,这是无可厚非的,也是值得肯定的。但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同时,尤其不能忽视人文素质教育。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人,技能和应用是第二位的,关键是培养人的思维,如何看待社会和自己,拥有怎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,这比技能更重要。现代社会在发展,高校培养的人才应该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。人不能变成工具,人是有思想,有精神追求的,在这个意义上,人文教育也许比掌握某项技能更重要。
何晶:您觉得目前学界存在哪些较突出的问题?您对于青年学人有怎样的期许?
徐真华:现在做学问不容易,年轻学者需要一颗安静的心。现在有些青年学者书读得太少,这和内心的躁动不安有关,希望很快能出成果,这样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出不了精品,学问处于比较浅的状态。年轻学者还是要静下心来,不能急于求成,目光要放长远。
另一方面,学术管理制度也需要改善,如今在用量化标准管理学术,制度层面并不利于学者安心做学问。学术环境如果不改变,学界的浮躁现象也较难有很大的转变。